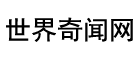《南史》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三(3)
蕴字彦深,彧兄子也。父楷,太中大夫。楷人才凡劣,故蕴不为群从所礼,常怀耻慨。家贫,为广德令。明帝即位,四方叛逆,欲以将领自奋,每抚刀曰:「龙泉太阿,汝知我者。」叔父景文常诫之曰:「阿荅,汝灭我门户。」蕴曰:「荅与童乌贵贱异。」童乌,绚小字,荅,蕴小字也。及事甯,封吉阳男。历晋陵、义兴太守,所莅并贪纵。后为给事黄门侍郎。
桂阳之逼,王道隆为乱兵所杀,蕴力战,重创御沟侧,或扶以免。事平,抚军长史褚澄为吴郡太守,司徒左长史萧惠明言于朝曰:「褚澄开城以纳贼,更为股肱大郡,王蕴被甲死战,弃而不收,赏罚如此,何忧不乱!」褚彦回惭,乃议用蕴为湘州刺史。及齐高帝辅政,蕴与沈攸之连谋,事败,斩于秣陵市。
奂字道明,彧兄子也。父粹字景深,位黄门侍郎。奂继从祖球,故小字彦孙。年数岁,常侍球许,甚见爱。奂诸兄出身诸王国常侍,而奂起家着作佐郎。琅邪颜延之与球情款稍异,常抚奂背曰:「阿奴始免寒士。」
奂少而强济,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。仕宋历侍中,祠部尚书,转掌吏部。升明初,迁丹阳尹。初,王晏父普曜为沈攸之长史,常惧攸之举事,不得还,奂为吏部,转普曜为内职,晏深德之。及晏仕齐,武帝以奂宋室外戚,而从弟蕴又同逆,疑有异意,晏叩头保奂无异志。时晏父母在都,请以为质,武帝乃止。
永明中,累迁尚书右仆射。王俭卒,上欲用奂为尚书令,以问晏。晏位遇已重,意不推奂,答曰:「柳世隆有勋望,恐不宜在奂后。」乃转左仆射,加给事中。出为雍州刺史,加都督。与甯蛮长史刘兴祖不睦。十一年,奂遣军主朱公恩征蛮失利,兴祖欲以启闻,奂大怒,收付狱。兴祖于狱以针画漆合盘为书,报家称枉,令启闻,而奂亦驰信启上,诬兴祖扇动荒蛮。上知其枉,敕送兴祖还都,奂恐辞情翻背,辄杀之。上大怒,遣中书舍人吕文显、直合将军曹道刚领兵收奂,又别诏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阳。奂子彪凶愚,颇干时政,士人咸切齿。时文显以漆匣匣箜篌在船中,因相诳云,「台使封刀斩王彪」。及道刚、曹武、文显俱至,众力既盛,又惧漆匣之言,于是议闭门拒命。长史殷叡,奂女婿也,谏曰:「今开城门,白服接台使,不过槛车征还,隳官免爵耳。」彪坚执不从,叡又曰:「宜遣典签间道送启自申,亦不患不被宥。」乃令叡书启,遣典签陈道齐出城,便为文显所执。叡又曰:「忠不背国,勇不逃死,百世门户,宜思后计,孰与仰药自全,则身名俱泰,叡请先驱蝼蚁。」又不从。奂门生郑羽叩头启奂,乞出城迎台使,奂曰:「我不作贼,欲先遣启自申,政恐曹、吕辈小人相陵藉,故且闭门自守耳。」彪遂出战,败走归。土人起义,攻州西门,彪登门拒战,却之。司马黄瑶起、甯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,奂闻兵入,礼佛,未及起,军人斩之,彪及弟爽、弼、殷叡皆伏诛。奂长子太子中庶子融,融弟司徒从事中郎琛,于都弃市,余孙皆原宥。琛弟肃、秉并奔魏,后得黄瑶起脔食之。弟伷女为长沙王晃妃,以男女并长,又且出继,特不离绝。
奂既诛,故旧无敢至者,汝南许明达先为奂参军,躬为殡敛,经理甚厚,当时高其节。奂弟份。
份字季文。仕宋位始安内史。袁粲之诛,亲故无敢视者,份独往致恸,由是显名。累迁大司农。奂诛后,其子肃奔魏,份自拘请罪,齐武帝宥之。肃屡引魏人至边,份尝因侍坐,武帝谓曰:「比有北信不?」份改容对曰:「肃既近忘坟柏,宁远忆有臣。」帝亦以此亮焉。后位秘书监。仕梁位散骑常侍,领步兵校尉,兼起部尚书。
武帝尝于宴席问群臣曰:「朕为有为无?」份曰:「陛下应万物为有,体至理为无。」帝称善。后累迁尚书左仆射。历侍中,特进,左光禄大夫,监丹阳尹。卒,諡曰胡子。长子琳,字孝璋,位司徒左长史。琳齐代取梁武帝妹义兴长公主,有子九人,并知名。
长子铨,字公衡,美风仪,善占吐,尚武帝女永嘉公主,拜驸马都尉。铨虽学业不及弟锡,而孝行齐焉,时人以为铨、锡二王,可谓玉昆金友。母长公主疾,铨形貌瘠贬,人不复识。及居丧,哭泣无常,因得气疾。位侍中、丹阳尹。卒于卫尉卿。子溥,字伯淮,尚简文帝女余姚公主。
铨弟锡字公嘏,幼而警悟,与兄弟受业,至应休散,辄独留不起,精力不倦,致损右目。十二为国子生,十四举清茂,除秘书郎,再迁太子洗马。时昭明太子尚幼,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,不限日数。与太子游狎,情兼师友。又敕陆倕、张率、谢举、王规、王筠、刘孝绰、到洽、张缅为学士,十人尽一时之选。锡以戚属,封永安侯。
普通初,魏始连和,使刘善明来聘,敕中书舍人朱异接之。善明彭城旧族,气调甚高,负其才气,酒酣谓异曰:「南国辩学如中书者几人?」异曰:「异所以得接宾宴,乃分职是司,若以才辩相尚,则不容见使。」善明乃曰:「王锡、张缵,北间所闻,云何可见?」异具启闻,敕即使南苑设宴,锡与张缵、朱异四人而已。善明造席,遍论经史,兼以嘲谑。锡、缵随方酬对,无所稽疑,善明甚相叹挹。他日谓异曰:「一日见二贤,实副所期,不有君子,安能为国。」引宴之日,敕使左右徐僧权于坐后,言则书之。
累迁吏部郎中,时年二十四。谓亲友曰:「吾以外戚谬被时知,兼比羸病,庶务难拥,安能舍其所好而徇所不能。」乃称疾不拜。便谢遣胥徒,拒绝宾客,掩扉覃思,室宇萧然。诸子温凊,隔帘趋倚。公主乃命穿壁,使子涉、湜观之。卒年三十六,赠侍中,諡贞子。锡弟佥。
佥字公会,八岁丁父忧,哀毁过礼。初补国子生,祭酒袁昂称为通理。累迁始兴内史,丁所生母忧,固辞不拜。又除南康内史,在郡义兴主薨,诏起复郡。后为太子中庶子,掌东宫管记。卒,赠侍中。元帝下诏:贤而不伐曰恭,追諡曰恭子。佥弟通。
通字公达,仕梁为黄门侍郎。敬帝承制,以为尚书右仆射。陈武帝受禅,迁左仆射。太建元年,为左光禄大夫。六年,加特进,侍中、将军、光禄、佐史、扶并如故。未拜,卒,諡曰成。弟劢。
劢字公齐,美风仪,博涉书史,恬然清简,未尝以利欲干怀。仕梁为轻车河东王功曹史。王出镇京口,劢将随之蕃。范阳张缵时典选举,劢造缵言别,缵嘉其风采,乃曰:「王生才地,岂可游外府乎?」奏为太子洗马。后为南徐州别驾从事史。
大同末,梁武帝谒园陵,道出朱方,劢随例迎候,敕令从辇侧。所经山川,莫不顾问,劢随事应对,咸有故实。又从登北顾楼赋诗,辞义清典,帝甚嘉之。
时河东王为广州刺史,乃以劢为冠军河东王长史、南海太守。王至岭南,多所侵掠,因惧罪称疾,委州还朝,劢行州府事。越中饶沃,前后守宰,例多贪纵,劢独以清白着闻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。
侯景之乱,奔江陵,历位晋陵太守。时兵饥之后,郡中雕弊,劢为政清简,吏人便安之。征为侍中,迁五兵尚书。
会魏军至,元帝征湘州刺史宜丰侯萧循入援,以劢监湘州。及魏平江陵,敬帝承制,以为中书令,加侍中。历陈武帝司空、丞相长史,侍中、中书令并如故。
及萧勃平,以劢为广州刺史。未行,改为衡州刺史。王琳据有上流,衡、广携贰,劢不得之镇,留于大庾岭。
太建元年,累迁尚书右仆射。时东境大水,以劢为晋陵太守。在郡甚有威惠,郡人表请立碑,颂劢政德,诏许之。征为中书监,重授尚书右仆射,领右军将军。卒,諡曰温子。劢弟质。
质字子贞,少慷慨,涉猎书史。梁世以武帝甥,封甲口亭侯。立太子中舍人、庶子。
侯景济江,质领步骑顿于宣阳门外。景军至都,质不战而溃,为桑门,潜匿人间。城陷后,西奔荆州。元帝承制,历位侍中,吴州刺史,领鄱阳内史。
魏平荆州,侯瑱镇盆城,与质不协,质率所部依于留异。陈永定二年,武帝命质率所部随都督周文育讨王琳。质与琳素善,或谮云于军中潜信交通,武帝命文育杀质,文育启救之,获免。文帝嗣位,以为五兵尚书。宣帝辅政,为司徒左长史。坐招聚博徒,免官。后为都官尚书。卒,諡曰安子。弟固。固字子坚,少清正,颇涉文史。梁时以武帝甥,封莫口亭侯。位丹阳尹丞。梁元帝承制,以为相国户曹属,掌管记。寻聘魏,魏人以其梁氏外戚,待之甚厚。
承圣元年,为太子中庶子,迁寻阳太守。魏克荆州,固之鄱阳,随兄质度东岭,居信安县。陈永定中,移居吴郡。文帝以固清静,且欲申以婚姻。天嘉中,历位中书令,散骑常侍,国子祭酒。以其女为皇太子妃,礼遇甚重。
废帝即位,授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宣帝辅政,固以废帝外戚,奶媪恒往来禁中,颇宣密旨,事泄,比党皆诛,宣帝以固本无兵权,且居处清素,止免所居官,禁锢。太建中,卒于太常卿,諡恭子。
固清虚寡欲,居丧以孝闻。又信佛法。及丁所生母忧,遂终身蔬食,夜则坐禅,昼诵佛经。尝聘魏,因宴飨际,请停杀一羊。羊于固前跪拜。又宴昆明池,魏人以南人嗜鱼,大设罟网,固以佛法祝之,遂一鳞不获。子宽,位侍中。
论曰:王诞夙有名辈,而间关夷险,卒获攀光日月,遭遇盖其时焉。奉光、奉叔,并得官成齐代,而亮自着寒松,固为优矣。莹印章六毁,岂鬼神之害盈乎?景文弱年立誉,芳声籍甚,荣贵之来,匪由势至。若使泰始之朝,身非外戚,与袁粲群公,方骖并路,倾覆之灾,庶几可免。庾元规之让中书令,义归此矣。奂有愚子,自致诛夷。份胤嗣克昌,特锺门庆,美矣。
明史·卷一百二十三·列传第二
原文: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,宿州人,仁慈有智鉴⑴,好书史,勤于内治,暇则讲求古训。告六宫,以⑵宋多贤后,命女史录其家法,朝夕省览。或言宋过仁厚,后曰:"过仁厚,不愈于⑶刻薄乎?"一日,问女史:"黄老何教也,而窦太后好之?"女史曰:"清净无为为本。若⑷绝仁弃义,民复教慈,是其教矣。"后曰:"孝慈即仁义也,讵⑸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?
"帝前殿决事,或震怒,后伺帝还宫,辄⑹随事微谏。虽帝性严⑺,然为缓刑戮者数矣。参军郭景祥守和州,人言其子持槊欲杀父,帝将诛之。后曰:"景祥止一子,人言或不实,杀之恐绝其后。"帝廉之,果枉。李文忠守严州,杨宪诬其不法,帝欲召还。后曰:"严,敌境也,轻易⑻将不宜。且文忠素贤,宪言讵可信?"帝遂已。文忠后卒⑼有功。学士宋濂坐⑽孙慎罪,逮至,论死,后谏曰:"民家为子弟延⑾师,尚以礼全终始,况天子乎?且濂家居,必不知情。"帝不听。会⑿后侍帝食,不御酒肉。帝问故。对曰:"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。"帝恻然,投箸起。明日赦濂,安置⒀茂州。帝尝令重囚筑城。后曰:"赎罪罚役,国家至恩。但疲囚加役,恐仍不免死亡。"帝乃悉赦之。帝尝怒责宫人,后亦佯怒,令执付宫正司议罪。帝曰:"何为?"后曰:"帝王不以⒁喜怒加刑赏。当陛下怒时,恐有畸重。付宫正,则酌其平矣。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。"
一日,问帝:"今天下民安乎?"帝曰:"此非尔所宜问也。"后曰:"陛下天下父,妾辱⒂天下母,子之安否,何可不问!"遇岁旱,辄率宫人蔬食,助祈祷。帝或告以振⒃恤。后曰:"振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。"奏事官朝散,会食廷中,后命中官取饮食亲尝之。味弗甘,遂启帝曰:"人主自奉欲薄,养贤宜厚。"帝为饬光禄官。
帝欲访后族人官⒄之,后谢⒅曰:"爵禄私⒆外家,非法。"力辞而止。然言及父母早卒,辄悲哀流涕。洪武十五年八月寝疾。群臣请祷祀,求良医。后谓帝曰:"死生,命也,祷祀何益!且医何能活人!使服药不效,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?"疾亟,帝问所欲言。曰:"愿陛下求贤纳谏,慎终如始,子孙皆贤,臣民得所而已。"是月丙戌崩,年五十一。帝恸哭,遂不复立后。 译文: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,是宿州人,仁爱慈善且聪慧明辨,喜欢史书,勤心于内治,空闲时就要求宫人们学习古人逸事。因为宋代有很多贤明的皇后,于是就让女史记下她们治家的方法,让六宫嫔妃从早到晚的研读。有的嫔妃说宋朝皇后过于仁厚,马皇后就说:“过于仁厚,难道不比刻薄更好吗?”有一天,皇后问女史:“黄老教是什么教,汉朝的窦太后却非常地喜欢?”女史说:“黄老教把清静无为作为根本。像弃绝仁义,让老百姓注重孝顺友爱,这就是它的教义。”马皇后说:“孝顺友爱就是仁义,难道有让人弃绝仁义却去讲究孝顺友爱的吗?”
朱元璋在前殿处理事情,有时非常生气,马皇后等到朱元璋回到后宫,常常依据事理委婉地劝阻。朱元璋的性格虽然刚毅,但因为马皇后的劝阻而能够减免刑罚的人也有很多。参军郭景祥守卫和州,有人告密说他的儿子拿着槊想杀他的父亲,皇帝(朱元璋)想要杀了他。马皇后说:“郭景祥只有一个孩子,别人告密的也许不是实际情况,杀了他恐怕就会断绝郭景祥的后代。”皇帝认为郭景祥非常廉洁,认真了解情况后,发现他果然是冤枉的。李文忠守卫严州,杨宪诬告他不遵守法律,皇帝想召他回来。马皇后说:“严州,是面临敌境的地方,随便的更换将领不合适。况且李文忠向来贤明,杨宪的话难道可以相信吗?”皇帝于是停止了这件事。李文忠后来终于建立了大功。学士宋濂因为孙慎的事情而获罪,被抓来定为死罪,马皇后劝阻说:“普通百姓家为孩子请老师,尚且将尊师之礼奉行一生,何况我们天子之家呢?况且宋濂住在家里,一定不知道实情。”皇帝不听。正好赶上皇后侍奉皇帝吃饭,马皇后不饮食酒肉。皇帝问原因。皇后回答说:“我在为宋先生作福事。”皇帝内心也感到凄然,于是放下筷子站起。第二天皇帝赦免了宋濂的死罪,把他安置到茂州。皇帝曾经让重刑犯筑造城墙。马皇后说:“通过罚劳役来赎罪,这是国家对待犯有重罪的囚犯的最大的恩惠,但本来就疲惫的囚犯如果再加重劳役,恐怕仍免不了死亡。”皇帝于是全都赦免了他们。皇帝曾经非常生气地责备宫人,马皇后也假装生气,让人送到宫正司定罪。皇帝说:“为什么?”马皇后说:“作帝王的不因喜怒而随意的赏罚。当您生气的时候,恐怕有所偏重。交付到宫正司,就能判定的比较合理了。也就是说陛下您定人罪也应该交付到有关的部门罢了。”一天,马皇后问朱元璋说:“如今天下的老百姓生活安定吗?”朱元璋说:“这不是你应该问的。”马皇后说:“陛下您是天下人的父亲,我有幸能成为天下人的母亲,孩子的安定与否,我怎么可以不问!”每当遇到灾年,马皇后就率领宫人吃粗茶淡饭,帮助百姓祈祷。皇帝有时把赈灾救济的事情告诉皇后,皇后就说:“赈灾救济不如事先有积蓄好。”有时朝廷官员上奏完事情,在宫廷中聚餐,马皇后就命令宦官拿来酒菜自己事先尝一尝。味道不好,于是就告诉皇帝说:“作为人主奉养自己应该差一些,奉养别人应该丰厚。”皇帝为此整饬了光禄官。
皇帝想寻找皇后的族人分封官爵,皇后拒绝说:“分封爵禄偏爱外戚之家,不合乎法律。”皇后坚决拒绝才停止了这件事。然而有时谈到父母早亡,皇后常常痛哭流涕。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睡觉得病。群臣请求祈祷祭祀,求取良医。马皇后对皇帝说:“死生,是命运的安排,祈祷祭祀有什么用处呢!况且医生又怎能使人活命!如果吃药不能见效,恐怕会因为我的缘故而降罪各位医生吧?”病情加重时,皇帝问他想说什么。马皇后说:“希望陛下能够求取贤能的人,听取别人的意见,自始至终,认真对待,子孙都能够贤能,大臣百姓都能够有所依靠罢了。”这月丙戌日去世,享年五十一岁。皇帝非常伤心,于是从此不再立皇后。
关于明朝《续忧危竑议》的问题!
续忧危竑议 郑贵妃 所谓“妖书”案,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。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名叫《闺范图说》事见《明史·吕坤列传》:“坤撰《闺范》,独取汉明德后者,后由贵人进中宫,坤以媚郑贵妃也。坤疏陈天下忧危,无事不言,独不及建储,意自可见。”的小书,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故事。这本图说以汉明帝马皇后为首,而马皇后又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,吕坤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,为郑贵妃以后当皇后找个说法。神宗偶尔翻见到此书,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。赐者无意,可受者有心。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以后,觉得可以利用它来做点文章,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,并且为之作序,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。事见《明史·后妃列传·郑贵妃》:“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,尝集《闺范图说》。太监陈矩见之,持以进帝。帝赐妃,妃重刻之,坤无与也。”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,其意在于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,加以宣扬罢了。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,大学士朱赓又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《续忧危竑议》的书,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,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,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,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,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。事见《明史·后妃列传·郑贵妃》载:“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,他日必易。其特用朱赓内阁者,实寓更易之义。”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,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,于是大朝廷兴冤狱,许多朝臣、百姓为此无辜受害,死于非命。然而,此案最终却不了了之。续忧危竑议